我是我父亲的女儿
我是我父亲的女儿
我是我父亲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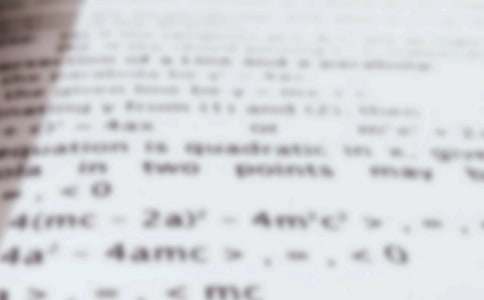
芭蕉雨声
书读出来以后,我就成了远离父母的游子。偶尔回乡,归途中总有乡人认出我来,我非明星脸,他们说出的是我父亲的大名,他们从我的貌相上一眼便断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惊喜之外,我欣慰我有一个到当教师的父亲。
父亲已退休十年,年届古稀。师范毕业的他一直在最基层的乡下做事,教书育人四十年。父亲说他想写写本乡教育史,原始资料和会议记录他都保存完好。我深知,即是没有这些备份父亲也能写出一部大书,心里有,自然下笔顺。
我读初中时,父亲是我的校长。校长的女儿,我没有傲气,只有忐忑,我不能给父亲丢脸。于是努力。熬灯油是常事。一次村里来了两个说书人,晚饭罢就在我家大门外开场了。我不去听,独自点着煤油灯温习功课。父亲悄悄走近,邀我出去,我想拒绝,他已搬着大椅子转身迈出门槛,我只好跟着。说的是《秦琼打擂》,围观者众,我踮脚也望不见说书者的鼓槌儿,父亲不言语,双手高举把我抱上了椅子。我居高临下,父亲含笑。
不善言辞的父亲,细敏,温厚。他有自己的体贴方式。他不常回家,却给我们姊妹五个都掖过被角,他掖的被角,平展舒适,密不透风。他熬的稀饭不稀不稠,带着香气。我读书没有形状,地面,阶矶,石板,随时委坐。每当此时父亲便不声不响地拿草垫过来,怕寒凉湿气伤我身。有一阵,我总是趿拉着鞋子,拖拖带带,他通过母亲转告我说女孩子要把鞋子提上,扣好鞋袢再走路。从此,我穿鞋没敢潦草过一回。
父亲做事慎密,治学严谨,为人实诚。我十来岁时,晚秋的夕照里,我跟着父亲去东坡的石板上收晾晒的'红薯干,最后一趟时天色已昏,父亲负重下山,我紧随。他一步一趋,前脚试探着踏实了,后脚才抬起。我有点不耐烦,蹦跳着欲超越他,一丛圪针挂破了我的袜子。是父亲在县城给我买的细线袜,枣红色,带花纹,我心疼得流泪。父亲放下肩上的重物,蹲下查看。摸着脚没伤到,就笑了,说回头再给我买一双新的。父亲没告诉我路该咋走,可我在那个秋天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从此学会了走路,走平稳的路。
赋闲在家的父亲,闲不住,养了十几只鸡,傍晚从草坡归来的鸡们,借院墙次第飞上高高的槐枝,父亲在树下慢慢扫拢散落的鸡粪,院子干净整洁,有淡淡的土气。鸡蛋攒着,谁回家谁吃,吃不完兜着走。父亲从冰箱里小心拾出鸡蛋,用草纸单独包好,码放在纸箱里,捆扎结实,可以大胆提拎,走多远的路也不会破损一枚。煮蛋,炒蛋,荷包蛋,城里的孙子孙女都说香,好吃。
展眼我已中年,父亲霜雪满鬓。每次回家,父亲出门迎我时总是欣喜里带着慌张,似乎我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他的公主殿下。脚边的小黄狗欢快地摇动尾巴,一声不吭。它一定嗅出来了,我跟它的主人是同一个味儿。
2011年9月2日8:3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