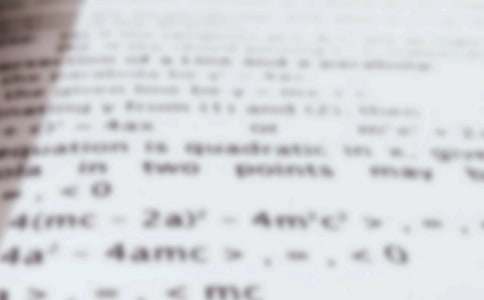无讼:“法”的失落-兼与西方比较上
无讼:“法”的失落-兼与西方比较(上)
在儿时的记忆里,长辈们关于“打官司”不光彩的教导可说是最清晰影像中的一幕;而在日常的生活中,民众对于法律的漠视和冷落又几乎是最寻常见闻的一例;但与此同时,各种媒介却在不断地传递着西方人好打官司的信息。的确,就各自法律传统而言,中国人的“厌讼”与西方人的“好讼”大约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此外,如果说西方社会对于“法”曾达到迷信的地步,那么中华民族在“法”的问题上则实在过于“理智”和“冷静”。很久以来,笔者常常疑惑于中西间的种种差异,亦时时忧虑国人观念上的'“厌讼”和社会对“法”的冷漠将阻碍当代中国法制的发展。当今之世,中华民族正需高扬法的权威,也亟待实现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在这种历史时刻,参照西方的情形对广大民众至今犹存的“厌讼”心理和我们民族对“法”的冷落传统做一番历史与文化的透视和反思,这或许是不无益处的。
一
从法哲学上分析,人类关于法的需要和知识不仅涉及“法律”,“法律”之外、之上还应当有“法”。两者之不同在于:“法律”是规范性的,“法”则是精神性的:“法律”是实用的,“法”则是超功利的:“法律”是政治的,“法”则是文化的:“法律”是行为规则的集合,“法”则是人类关于生活秩序的基本信念和精神原则的总汇。同时,“法”是“法律”的价值依据,它高于“法律”,并植根于人类心灵的深处:“法律”则当是“法”的产物,并受其统辖。惟其如此,方能有“法治”社会的出现。1
就人类已有的历史来看,“法”与“法律”及其相互关系在不同文化的传统之中有着不同的命运。这在中西方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法”与“法律”常常分离(其经典表述形式是“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法”高于“法律”,其原本涵义是理性、正义、自由、幸福与规律,它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并且是普遍的、永恒的:“法律”必须符合于“法”。文艺复兴以后,“法”更成为世俗社会的宗教替代品和上帝的世俗化身,取得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权威,因之,“合法性”的考察便成为西方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一切个人的行为和集团的活动皆须“合法”,而且一切阶级的统治与最高统治者的言行也须“合法”,甚至一切现行的“法律”亦要“合法”,于是,在西方法律传统中便有了“暴君”与“恶法”的概念,更有了“暴君非君”与“恶法非法”的命题。
而中国传统则不同。自先秦以来,“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所以西方人崇拜“法”,中国人则崇拜“国家”和“权力”);于谋求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而言,首要的是取得政权,合不合法则在其次,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便是这个道理。至于“法律”本身,只要它依附于王权,就根本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
说中国传统中有“法律”而无高于“法律”的“法”,或许有人会提出反驳,理由是:中国古代有“天理人情国法”之说,民众之中则有“王法”观念,思想史上亦有道家之“自然法”、墨子之“法天”与荀子之“以类举”等等。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上述种种观念都不是“法”。
1关于“天理、人

2关于“王法”观念。中国古代民众的确时常高呼“王法何在”,但这种“王法”不过是现实法律的直接观念化;民众于“王法”的价值期望也与现实法律无异:几乎只是“安全”和“秩序”;同时,“王法”在民众观念中之所以有权威,也仅仅因为它是“王法”-有至高无上的王权做后盾;人们呼唤“王法”,实是呼唤王权的有效干预,呼唤现实“法律”的正常实施。“法”则不同,它凌驾于全社会之上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