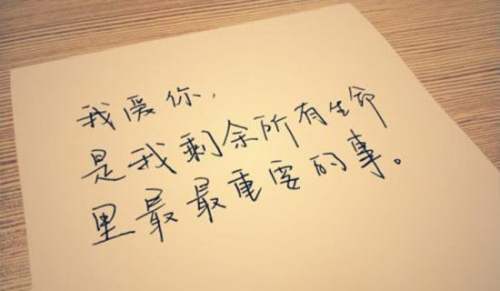孟荀新论
孟荀新论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姑且将"自我"动物性的一面名为"欲我"而将其规定人之为"人"的一面名为"仁我",则孟子显然以为二者皆是作为宇宙本体的"天"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赋予人类的某种本能――在"天"无非必然性的安排而在"人"则为选择的自由;自觉的人只将动物本能所规定的"自由"看作必然性的限定而将"仁我"相对于"欲我"的自由视为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仁义乃人之安宅和正路,当"君子"依天道所趋努力实现"仁我"所规定的自由之时也正是自觉地履行某种冥冥之中的"绝对命令"。"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欲我"所摄之"耳目之官"以? 偶??晕遥??????髦链丝?羯?煌蛳蟮?quot;现象界";与之相连的"欲我"在高等动物乃是正位而对于已达"本体界"的"人心"而言则为自我之沦落。唯有在"思"的过程中当"仁我"以高度的主宰心与"欲我"形成相互制约的共轭关系之时,自我方可体验后者所隐涵的"异化"的压力以及前者以其君位所确立的"我在――两种趋势相反相成,构成内在于自我的矛盾。获得"我在"的人正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的"大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心"无非"仁我"受制于"欲我"之时的异化形态,当其随"欲我"之寂灭而恢复本真之时即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此乃人类之性天。作为自然演化之势能的"天"如同一条纽带将无机物、有机物、微生物、植物、低等动物、高等动物以及人类连为一体,物类各安于高低不同的势位。唯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可栖居自然演化的最高势位――"本体界",亦可随"仁我"之障蔽而沦落高等动物所栖之"现象界"。人类因其可以栖居生命进化之流的两个不同的势位故而常生"主客二分"之感。而当其回归正位之时即与化育宇宙万物的`"天道"融为一体,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尽心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告子上》)。规定人之为"人"的"仁我"可由浑朴稚拙的赤子之心得以完美地展现,而后随着心智的发育逐渐退居心理深层的下意识――日积月累的外在闻见将"仁我"裹于其中,构成心理结构中的表层意识。夜晚合眼之后,由闻见所构成的表层意识因与外境绝缘逐渐寂灭,"我"亦随之回归日间退居下意识的原初自我――此时若还残留微弱意识则在内心的视屏中显现为奇幻的梦境。孟子以为"欲我"与"仁我"昼夜轮休,日间与外境相接时放失本心而仅赖夜气存养则与禽兽相去不远。"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自我由其原初状态沦落外境之后,尚未泯灭的本心下意识也显现仁、义、礼、智"四端"。孟子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

[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