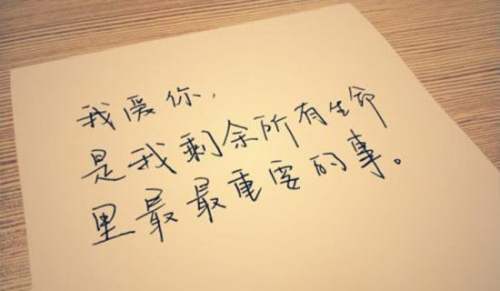文化美、前文化美与复合美
文化美、前文化美与复合美
与美学中的其它重大问题一样,美的分类,也是美学史上一直没有规范解决的问题。我国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是根据审美对象自身性质的分类,如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形式美等等。这种分类,其最大缺陷是把“美”的分类变成对“美的事物”的机械归类,没有也无法揭示美自身的不同生成特征和规律,因而,也无助于对客观美的认识、分析与把握。这与传统美学对美的性质的机械理解相关。从系统美学角度讲,美是不能脱离审美关系系统①而独立存在的,美只是审美关系中客体的系统质。在现实中,离开特定审美对应关系和审美主体,离开特定审美距离和审美环境,客体便无所谓美或不美;美决不是客体固有的自然质或社会功能质。因此,美的分类是不能脱离开审美系统的。当然,如果我们根据科学抽象原则,设定人类类主体为审美主体,同时将审美系统的诸要素--审美距离和环境等等“悬置”,客体或客体因素②的审美价值或美依然是可以相对确定,并进行分析研究和分类把握的。但显然,这种抽象的美的分类,决不是依据客体自身的特征与性质,而是依据审美关系生成的性质。③据此,我将美划分为,前文化美,文化美与复合美三大类。笔者认为这一新的分类方式既有助于美学学科的规范,也有助于我们对美学和艺术现象认识的深化。一
审美系统中的主体是人,而人的生命从属于“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④人的生命本

所谓文化美,也就是传统美学所讨论的美,即由“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生成的美,所物化和表现在客体身上的文化审美价值。文化审美关系发生于人类与动物相揖别的漫长进化过程中,生成于人类类意识、类自觉的形成和体现类自觉的自由创造--“劳动”的过程中;文化审美既伴随人类类本质生成而生成,又体现着人类的文化特征。动物能本能地趋利避害,建巢筑穴,但却不能像人类那样,顺势利导,化害为利,能动地为自己创造更新更美的生活环境,因此,动物没有“文化”,也不会对客体内含的“文化”有任何兴趣--甘肃的“阳关”遗址,甚至连鸟儿也不愿栖息。但对人类来说,先民们艰苦创造的文化遗痕,是自然界、动物界任何精妙建构所不可比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存在。这便是“阳关”文化魅力之所在--它所凝聚的是中华文明沉积千百年的历史,它所唤醒的是中国文人代代承传的思古怀古情结。文化审美是人类的“专利”,也是审美的本质构成。
所谓前文化美,系指客体因满足主体潜能本能需求而获得的审美价值。当然,这种前文化美的获得,只能是在人类审美系统整体生成存在的条件下。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仅仅停留在物理、生理、心理水平上,并不存在主客体关系或审美关系,而只有动物与自然的适应关系。动物与自然是直接同一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对象性的关系、更不存在享受性体验自己潜能、本能的“审美关系”。蝶恋花肯定不是审美;一只母猴喜欢上另一只公猴,当然也不是审美。但人类在从消极适应自然到能动改造自然的漫长过程中,一面不断改造自身的感官结构,生成“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一面丰富发展自身的感觉,使之“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⑤从而将人的本能潜能需求从被动性、适应性动物水平提升到能动性、主动性人的水平,并伴随着肯定自身本质力量的文化审美关系的生成而获得审美性质,使前文化动物性适应关系成为人类审美系统的构成部分。⑥因此,同样是对色彩和花的喜爱,人恋花成为高雅的审美活动;虽然是与猴子“同宗”,人对异性的关系便具有了审美意义,甚至如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所比喻的,人类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