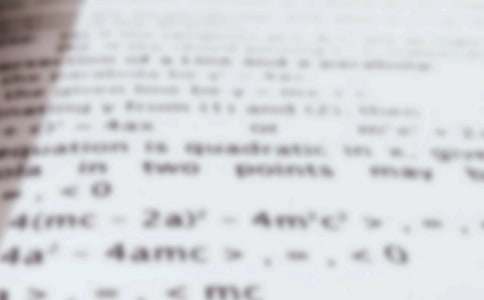北山秋色
北山秋色
北山秋色武漢市黃陂區三中 高深貴
周日,我回到北山老家,在教書的二哥家吃過午飯,告別在他家吃過飯立即開始牌局的同仁。回到上灣,已是正午1:30,從下灣到上灣兩裏路,只在巷子沖口看到家林四伯和喜枝大媽一前一後向店上走去,再沒見一個人。四伯是光漢條,先是和自己當工人的二哥共著二嫂,讓著他的二哥死了,疼愛他的二嫂老了,他就和剛死了丈夫的喜枝大媽打得火熱。
回到村裏,只在隊長運叔

我走到村北,準備到山上轉轉。
北邊原來空空的菜地,現在已長滿了板粟樹落光了葉子,園周圍是並不興旺的蘆葦和荊棘、杉樹。
向北是揚子沖,過去光禿禿的山坡,現在難以見到白沙了。長滿了松樹,放水的池口早進行了加固,水泥和石頭做的。原來的放水溝更深了,有的改了道。水的切割能力真強,特別是對結構鬆散的沙土,這真正是以柔克剛啊!
揚沖小水庫自從發大水衝垮以後,分散的農戶再也沒能團結起來,修復這個水庫,缺口的堤壩於是徹底的坍塌,把下面的兩個冷浸田變成了白沙灘,長期的荒涼又使雜草們找到了繁衍的好地方,現在白沙灘早已成了綠草地了。地主運叔和財叔又把它們都種上了板粟,現在,青青的草地又是茂密的板粟林,地上落滿黃葉和刺坨。板栗樹葉大部分掉了,還有一部分堅守著,更顯得樹林的幽深神秘。
沙塘上和山坡上的田地,都是收穫過的蒼白和荒蕪,讓人靜得發慌。
快到大堰堤埂,路口卻被人用荊棘封鎖了,只好退轉來,岔到山上,從石上過來。沒想到,生活就在平靜中悄悄地發生著巨大變化。
過去,大堰埂上除了幾棵桐樹外,沒有雜樹,草是清一色的淺絲毛和鐵絆根,現在卻雜草叢生,灌木滿坡,讓人總懷疑樹棵裏草底下石頭中,藏著什麼厲害的可怕的東西。清冷的山風從荒草和黃荊條上刮過,發出低沉威嚴的嘯聲。
水蕩漾著,拍打著堰壩,從石頭縫裏發出哐鐺哐鐺空洞的水聲。
山林靜悄悄,只剩下一陣陣單調的松濤。
沿堰裏大路,我來到堰尾的張沖。那裏的田地,都荒蕪著,長滿了低矮的鐵絆根草,一叢叢燈芯草沖天而立,到處是牛腳印和牛屎。沖中兩個小廢田裏長有野荸薺,被野豬翻個遍,象被犁過一樣。兩擔多田裏,只有鬥把田被我父親用刺藤圍起來,種了一些芝麻和蘆筍。
山坡上,松樹青色的樹枝週邊總雜有一些黃色的松針,那是快要衰落的老松針。綠色的山林中紅色、橙色、黃色的油梓,在風中搖曳生姿,煞是好看。
原來的小松樹,現在都長高了,到處是手臂粗,大腿粗,碗口粗的樹,高高地聳立著,高樹底下,則是高高矮矮的灌木。
風一陣陣地來,林濤一陣陣地響。動過響過之後,又是一陣無邊的靜,引人沉深思遐想。
同為楓樹,有的青綠蓬勃,有的紅葉蕭蕭,有的綠中泛著金黃;長在田梗山坡上,油籽樹葉子掉落,稀疏的油籽在陽光中閃著潔白的光芒。
一株瘦高的楓樹,在半山坡高高地超出瘦削的松樹,深透的紅葉高挺著沖向青天,非常顯眼。風來的時候,在綠色的海洋中顯出萬種風情。
沖上,是菩薩窪水庫,壚口下水聲潺潺,但流到岩下的沙溝中,就逐漸消失了。溝裏的幼松特別青綠,綠得使人陶醉。
水庫堤壩下的石崖中長著十分繁茂的灌木藤蔓,我在地上發現了鱗片非常粗大的蛇蛻。於是,我放棄了到崖下石洞一探的計畫,上到山坡上。
山坡上,紅蜻蜓、黃蜻蜓、綠蜻蜓起起落落,飛飛停停。荊棘長長的藤條上結滿了青青黃黃的刺果。松樹上舊的黑黑的松球未落盡,新的青青的結實的松球又在枝上搖晃。落到地上的松球都松松地咧開著,飽經風雨烈日摧殘,腐朽,黑暗,陳舊。
白沙坡黑石縫中,紫色的花正開著,沒有什麼水色,毛茸茸的。即使在生命最燦爛的季節,也只如此的平淡,我不禁長歎,這過的是什麼日子!這些平原沃野裏競爭失敗者,以為逃到這艱苦的地方,再不會有競爭對手,可以過幾天自在輕鬆的日子,卻不料在這幾乎完全沒有土壤和水分的石頭縫中,競爭更加慘烈,好不容易紮下根,那蔸同樣是競爭失敗者的茅草,也來到這裏紮了根,並要將它排擠出去,它只好深紮下根,最後和茅草在這裏同縫共生,都苟且地活下來,都長不好,但又都無路可退,只好這麼將就,在慘烈的競爭中苟活下來。
下到沖裏頭的沙灘中,沙灘中那個黃土堆長滿了松樹和楓樹,格外繁茂,路兩邊樹林裏,落滿了松針和其他樹葉,滿是腐殖質。
我坐在沙灘中的鐵胖根草上,一隻鮮豔的毛蟲興高采烈地爬行著,我一腳踩死了它,它立即變成了一片青綠的泥漿。
看著它,我忽然感到生命的悲哀,小動物之於大動物,小百姓之于大幹部,單個群眾之于龐大的國家機器,個體的生命相對于漫長歷史長河,是這樣無奈、無助,渺小、短暫、微不足道,噩運降臨無聲無息。
一隻細小的蟲爬上我的膝蓋,我一指彈飛了它。仔細一看,安靜的地面,滿是活躍的生命,看起來,我每坐一下,每走一步都會殘害許多生命,只是我不知道罷了。
一根野雞毛!根部還有血,靠柄部分的毛被弄得稀爛,整根毛一米多長,看來這只公雞是受到突然襲擊,猛地飛起尾翎被壓住而扯掉的。美麗修長的尾巴既是招來母雞愛情的法寶,也是招來災禍的根苗和逃難時的負擔。
又到了那個近山頂的石頭旁,十幾年前的那個秋夜,我披著大衣,在這個石頭上守了一夜,打野豬,那只拴在山頂崗上的狗,在朦朧的月色中,在空曠孤獨的夜裏,給我極大的`支持和安慰。靜靜的月光,陣陣的松濤,狗向遠方低低地吠著,不久,近處的樹林中傳來輕微的沙沙聲,不知是野豬,還是野狗的走路聲,被拴住無法逃離的狗輕搖著尾巴,低垂著頭,耷拉著耳朵,嘴裏發出低低的討好的似小兒啼哭的聲音。我緊握著獵槍,卻不見野物出現,忍不住僵持緊張,我輕咳了一聲,沙沙聲遠去,狗兒又恢復了平靜,原來狗也是很機靈的,善於見風使舵,在強敵面前還是能搖尾氣憐的圖生存。我想,大概動物也能思考,也有感情,並非只有本能。
山茶花深綠的葉子閃著蠟光,潔白的茶花開著的開著,零落的零落,讓人生出無限的憐惜。
大堰的水,因為喂魚,再不是原來那麼清澈了。水面浮著魚吃剩下的草梗。在有草的地方魚時時翻起水花,跳躍翻滾,原來清澈碧綠的大堰,現在骯髒得很,據說天熱臭不可聞。
下灣的全哥承包了大堰,在堰旁邊做了房子,周圍的水田山地都成了他的牧場,喂牛喂羊。說是承包,上十年了,全村人卻沒看到一片魚鱗。
大堰裏邊石頭上原來是我們夏天洗澡的地方,現在卻再也沒人洗冷水澡了,沒有了青壯年在家,老年人不敢洗。小孩,村裏沒有了。青壯年帶著他們的妻子兒女湧向了城市,並安了家。
轉回村裏,已是下午四點多鍾,村裏一個人都沒有,田畈裏也看不到。
我不知道人們幹什麼去了。
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故鄉來,我不是那個迅哥兒,也看不到閏土,看不到豆腐西施、圓規,更沒有了水生。當然我的“宏兒”和我的兒女們都已經不再嚮往這般靜寂的山村,他們有做不完的作業,玩不厭的電子遊戲,不願意回,所以,只有我回。
我不知道,我們這一代百年之後,我的故鄉,還有人煙麼?
2005年10月4日于蔡店一稿
2005年11月1日於三中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