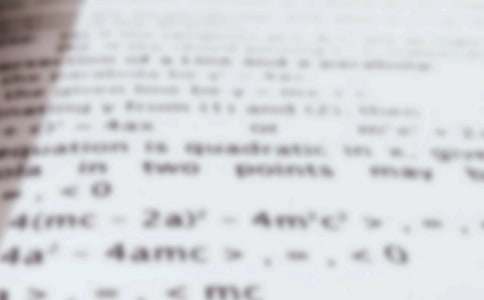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推荐3篇)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篇一
《墨经》是墨子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其中,“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墨经》中“谓”的含义。
首先,从字面上理解,“谓”是指言语中的陈述、表达的意思。在《墨经》中,“谓”被用来表示人们对事物进行评价、判断、描述等行为。例如,在《墨经·尚同》中,墨子说:“天有高下,地有远近,人有贤愚,事有利害。”这里的“有”可以理解为“谓”,表示对天、地、人、事物的评价和判断。通过“谓”,墨子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理解和价值观。
其次,从墨子的思想体系来看,“谓”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墨子强调“兼爱”和“非攻”,主张消除战争和社会不公。在他看来,“谓”不仅是对现实的评价和判断,更是对人们应当追求的道德标准的表达。墨子认为,人们应当根据道德原则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通过“谓”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强调道德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为道德规范是人类共同遵循的准则。因此,在《墨经》中,“谓”也承载着墨子对道德的渴望和追求。
最后,从实践层面来看,“谓”在《墨经》中还有着实际应用的意义。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改革方案,他认为人们应当通过实践来实现“兼爱”和“非攻”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评价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通过“谓”来指导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墨子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而“谓”成为了这一实践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和指导原则。
总之,《墨经》中的“谓”既是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也是对道德原则的表达和追求,同时还是实践中的指导准则。通过对《墨经》中“谓”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墨子的思想和墨子学派的核心理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启示,指导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为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篇二
《墨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中的“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墨经》中“谓”的含义。
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谓”在《墨经》中常常用来表示陈述、表达的意思。墨子在《墨经》中通过“谓”来表达对事物的评价、判断和描述。例如,在《墨经·尚同》中,墨子说:“天有高下,地有远近,人有贤愚,事有利害。”这里的“有”可以理解为“谓”,表示对天、地、人和事物的评价和判断。通过“谓”,墨子表达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和见解。
其次,从墨子学派的思想体系来看,“谓”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墨子主张“兼爱”和“非攻”,提出了一套道德准则和社会改革方案。在他看来,“谓”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评价和判断,更是对人们应当追求的道德标准的表达。墨子认为,人们应当根据道德原则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通过“谓”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强调道德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认为道德规范是人类共同遵循的准则。因此,在《墨经》中,“谓”也承载着墨子对道德的渴望和追求。
最后,从实践层面来看,“谓”在《墨经》中还具有着实际应用的意义。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改革方案,他认为人们应当通过实践来实现“兼爱”和“非攻”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评价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通过“谓”来指导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墨子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而“谓”成为了这一实践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和指导原则。
总之,《墨经》中的“谓”既是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也是对道德原则的表达和追求,同时还是实践中的指导准则。通过对《墨经》中“谓”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墨子的思想和墨子学派的核心理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启示,指导我们的思考和行动,为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篇三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的论文
摘要:“谓”是《墨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其本义而言,“谓”就是“报”:作为动词,是指主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之实情的基础上,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的行为;引申为名词,指的就是“报”的内容。后期墨家在坚持“以报释谓”的基础上,在名学论域中对“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他们对“谓”概念的理解和探讨,实际上是对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的提炼和深化。
关键词:后期墨家;墨经;谓;报
“谓”是《墨经》中联结“名”、“实”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准确把握“谓”的含义,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后期墨家的名学思想。自上个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墨经》中“谓”概念的含义已有不少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认为1、“谓”是动词,《墨经》中“谓”的三种形式(移、举、加)可以与英文中的系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相对应。[1]2、“谓”既可以作动词,指“特定对象的具体言语活动”[2];也可以作名词,指“一种简单陈述句的表达形式”[3]。3、“谓”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命题。[4]4、“谓”表判断,是思维的内容。[5]5、“谓”相当于“谓词”,是判断的谓项,句中的谓语。[6]这些从现代语言学或逻辑学角度对“谓”的解释,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墨家“谓”概念的理解;但由于过多地强调“谓”与现代学科中某些概念的表面相似性,似乎对“谓”在先秦时的本来含义关注不够。因此,本文试图从“谓”的本义和在先秦时期的一般使用情况入手,通过分析墨家学派名实观的演变,来进一步探求《墨经》中“谓”概念的含义。
一、“谓”的本义
“谓”是一个相当后起的`形声字。在先秦出土文献中,“谓”一般假借为“胃”字。根据《说文》“谓,报也,从言,胃声”[7],可知在许慎看来,“谓”的本义是“报”。“报”有“告”的意思,虽不从言,但也可以表示一种言说行为。例如“子贡还报孔子。”(《庄子·渔父》)“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庄子·应帝王》),其中的“报”指的就是“报告、告诉”。不过,“告”并不是“报”的本义。从古字形上看,“报”为会意字,有惩罚、治人罪的意思。《说文》云“报,当罪人也”[8],又曰“当,田相值也”[9]。“当”有“对当、对等”之意,可见“报”的本义似指“根据犯人之罪行而处以同等之刑罚,或以同等之刑罚来表达对某罪行之态度”。其意重在“相当”或“对等”。从字例上看,先秦典籍中的“报”字大多与其本义的用法相似,表达的是类似于“以与某物相对等的他物回报之”之类的意思,而不从“告”义。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报虐以威”(《尚书·吕刑》)、“报怨以德”(《老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荀子·正论》)等等。
从“报”的本义和先秦时期“报”字的用例来看,“报”有如下特征:1、“报”一般有两个成分:一个是“报”的对象,一个是“报”的内容。这两个成分在逻辑上有先后之分。例如“报虐以威”,是先有“虐”,再以“威”报之。2、“报”具有主观性,反映了这一行为的发出者对所“报”对象的认识和态度。例如,对于相同的对象“怨”,可以“报之以德”,也可以“报之以直”。“报”之对象是已有的事实,而“报”的内容则取决于主体的认识、态度和意愿。3、“报”的两个成分虽然性质不同,但客观上都以追求某种对等性为目的,有“当”的内在要求。4、“报”作名词时,是指“报”动作的内容。如“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爵位、官职、赏罚,都可以成为对某些行为或现象的“报”。
从“报”的本义出发,结合出土文献中假“胃”为“谓”不从言的事实,我们可以推知先秦时期的“谓”字不只是一种言说行为;“谓”的含义可能与“报”的本义有更密切的关系,具备与“报”的本义相类似的特征。
二、“谓”的用法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
谓”在先秦时期的用法进一步加深对它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先秦时期的“谓”字句(即以“谓”为核心动词的语句)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谓”必带有“a”、“b”两个不同的成分,并且所有句式都可还原为“谓ab”这一基本句型。[10]结合上文所论“谓”之本义,可知“a”、“b”之中应有一个成分

第一种情况,对象是人。例如:1、《庄子·盗跖》:“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此句中“子”、“我”为天下人“谓”的对象,若“子”、“我”之实为“盗”,则可谓之“盗丘”、“盗跖”。2、《荀子·臣道》:“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此句中“伊尹”、“周公”为“谓”之对象,由二人具有“圣臣”之实(这是言说者的主观判断),则可谓之“圣臣”。3、《论语·公冶长》:“孰谓微生高直?”此句中“微生高”为“谓”之对象,孔子认为他没有“直”之实(“直”的品格),因此提出怀疑。
第二种情况,对象是物。例如:1、《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此句中“乳”指某食品,“虎”指某动物,“乳”与“谷”是对同一食品的不同叫法,“虎”与“于莬”也是对同一动物的不同称谓,对象之“实”就是其自身之形貌等特征。2、《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擁肿,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规矩。”此句中“之”为代词,代“谓”之对象,“大本”云云,即是对象之实。
第三种情况,对象是现象或事件。例如:1、《尚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此句中“时”通“是”,代指一种现象,“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即为这种现象之实情,言说者将此种现象称为“巫风”,“巫风”即“谓”之内容。2、《墨子·七患》:“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此句中前一个“之”字代指一种现象,“一谷不收”为此现象之实情;言说者将其称之为“馑”,“馑”即为“谓”的内容。后半句之结构与前半句相同。
第四种情况,对象是行为。这种情况与上述第三种情况类似,例如:1、《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醉而不出,是谓伐德。”2、《老子》:“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3、《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4、《孟子·滕文公上》:“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
由以上例证,可归纳“谓”的用法如下:1、“谓”必有对象;2、对象必有实情;3、言说者(或隐或显)根据实情,对对象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
综合《说文》对“谓”的解释以及“谓”的用法,“谓”概念的含义可以概括如下:“谓”就其本义而言就是“报”,指主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之实情的基础上,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的行为。引申为名词时,“谓”指的就是“报”的内容。ゼ叶浴拔健钡牟发
“谓”在《墨经》中共出现66次,但与其含义相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条:1、“谓,移、举、加。”(《经上》);2、“谓:狗,犬,命也;狗犬,举也;叱狗,加也。”(《经说上》);3、“无谓则无报也。”(《经说上》)由“无谓则无报也”,可知后期墨家对“谓”的理解并没有偏离其本义。那么,所谓“谓,移、举、加”又当作何解呢?笔者认为,这是后期墨家在坚持“以报释谓”的基础上,在名学论域中对“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是对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的提炼和深化。
首先,“谓,移、举、加”一条出现在以概念界定为主的《经上》中,且紧接“名,达、类、私”,可知本条虽然是后期墨家对“谓”的专门论述,但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名”紧密相关。《经上》“所谓,名也;所以谓,实也。”可视为另一佐证。
其次,墨子的名学主张中其实已经提及了“移(命)”、“举”、“加”,只是不够系统。例如在论及名的产生时,墨子提出:“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勉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
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非攻下》)“义”的含义是明确的,就是“圣王之法”(即兼爱非攻)。而天下的诸侯行“攻伐并兼”等不义之实,却仍然拥有“誉义之名”;在墨子看来,这显然是人们“不察其实”而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因此,就“名”的生成而言,对待各种现象和行为要“察其实”而后“有其名”,对各种事物则应“分其物”而后“命其名”。
在论及名的使用时,墨子说:“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天志上》)“暴王”是已有之“恶名”,用“暴王”之名来称谓那些“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的诸侯国君,正是表达了墨子以“名”来分辨和评价对象的用名主张。
由上可见,在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中,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通过对象获得名,以及通过名认识、分辨和评价对象的建构存在,而“命”、“举”、“加”是其中的关键词。后期墨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命”、“举”、“加”重构了“谓”的含义,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系统表征“命名”、“举实”和“用名”的名学概念。
“命”,就是据实命名。例如谓“狗”为“犬”。“狗”在这里不是指称一个语词,而是指称命名的对象,属于语词的正常用法;“犬”指的是语词本身,即“犬”这一名称。看见一种动物,根据其实(如形貌等特征)将其命名为“犬”,这就是“命”。由其过程表现为将对象之“实”转以语词之“名”代替,因此也称为“移”。与此类似的,如“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经说上》)等等。其中的“命”都是指根据对象之实进行命名的行为。
“举”,即《小取》篇所说的“以名举实”。“举”的本义是“双手托物”,《墨经》又以“拟实”释“举”,都是为了说明“举”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名来比拟实,或通过名来再现实,也即荀子所谓“名闻而实喻”(《荀子·正名》)之意。“举”可以看作是“命”的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举出来的“名”仍然是命名时的含义和指称,是“有固实”之名,因此《经说上》云“狗犬,举也”,即在强调其含义和指称的确定性。又如“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天志上》),“圣王”或“暴王”之“名”所对应的“实”都是确定的,即“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或“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用前者之名,意在举出或再现后者之实。
“加”,是将所举之名运用到具体语境中的行为。“名”产生于特定对象,但从其产生之时起,又必然与其命名时所据之对象相脱离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加”的过程,就是将这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公共之名”重新加以具体化,以指称新的对象的过程。所举之名一旦运用到具体语境中,就由静态之“名”转成了动态之“谓”,有了新指称对象,并体现出言说者的主观意愿和认识。例如《墨子》中的“圣王”之名,本产生于“禹汤文武”等特定的对象,但一经产生后,就可以用来指称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的诸侯。以“圣王”之名来指称这些诸侯,就是“加”。
我们可以通过《墨子》书中的原例来区分这三种“谓”的不同,例如:“禹汤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谓之圣王。……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天志上》)按照上文的辨析,可以将此节中的“命”、“举”、“加”区分如下:
命谓部分
对象:禹汤文武
对象之实: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命名:圣王
举谓部分
以名:圣王
举实: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加谓部分
所加之名:圣王
所指之实: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
指称对象:当时
的诸侯国君
析而言之,“圣王”在命名时具有确定的含义(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和所指的对象(禹汤文武),在“以名举实”的过程中也仍然保留了命名时所对应的“实”。到了“加谓”阶段,“圣王”之名便有了新的“实”(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等等)和指称对象(当时的诸侯国君)。因为新的“实”与“圣王”之名原有的“实”相对当(均可归结为“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因此可以将“圣王”之名加在新的对象(当时的诸侯国君)上,用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认识和态度。
综上,可知后期墨家并没有偏离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基本思想;只不过他们将这一整套过程简化成了“命”、“举”、“加”这三种“谓”的形式或环节。后期墨家对“谓”概念的细化和扩充,其实是对墨子名学主张的精致化和系统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谓”在先秦时期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而又有独特意味的语词。一方面,它与“言”、“语”、“曰”、“云”一样,作为言说行为的表征动词,在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它又不是普通的言说动词。作为联结“名”与“实”的桥梁和手段,“谓”自有其独特的内涵和使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拿现代学科中的某些概念来比附。同样,作为先秦时期唯一对“谓”有过专门论述的学派,后期墨家对“谓”的理解和运用也与当时的语言使用背景和他们的学术渊源密切相关;如果不将这些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我们对《墨经》中“谓”概念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オ
参考文献:
[1]谭戒甫:《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104页。
[2][3]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308、311页。
[4]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5]詹剑峰:《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6]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第二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7][8][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惟贤整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867、1211页。
[10]朱承平:《先秦时期的“谓”字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