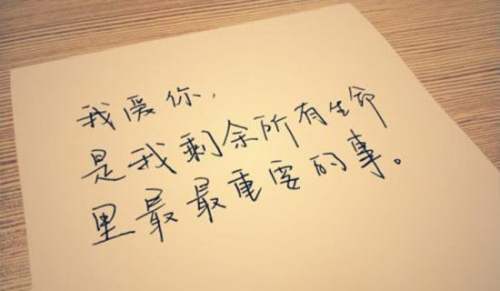与索尔曼先生谈中国法治
与索尔曼先生谈中国法治
“醒客”是万圣书园开的一家咖啡店的名称,仿着英文“thinker” 的读音而取名。万圣书园是一家很具品味的书店,毗邻北大清华和中关村,因此一些学术书在这里销量很好。我个人的幸运是就住在这家书店的楼上,下楼即可进书店,买书甚是便利。同时,醒客也是一个与友人或来访者谈天的好去处。伴着悠悠的背景音乐,喝一杯咖啡或新茶,饮品的香气与书香混合在一起,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窗外的绵绵细雨,思绪也平添了几分诗意。
10月18日的客人是一位法国学者,Guy Sorman博士,他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学家和评论家,法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他自己名下的出版社(Editions Sorman)的总裁。索尔曼先生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了,为的是写一本有关中国人权以及法治进展的书。他要跟我交流的主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另外还有死刑问题,这也是许多西方人权人士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索尔曼对于中国法律的历史颇有兴趣,他好奇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传统的制度与观念在今天的法律生活中有怎样的影响和价值。这当然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跟他说起自己的一些看法,在书本法律的层面上,当然是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百年来的变法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作三个阶段:1905-1949年是模仿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时期,这个期间仿照欧陆尤其是德国的模式形成了一个西方化的法律体系。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8年,是法律的苏联化以及法律虚无的时期。有人愿意把这个时期的前十年说成是一个建设苏联式法制的阶段,后面的二十年才是法律虚无时期。我个人认为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必要,首先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学习本身就是有口无心的,只有一部宪法和一部婚姻法颁布出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退一步,即使我们认真地学习,五十年代的苏联也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模仿秀”再逼真,也不过是非法治国家里的大姐与二姐而

我跟客人提到了著名汉学家艾斯嘉拉(Jean Escarra),上个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的法国法学家,他对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在法律上的差异有很敏锐的观察。在《中国法》一书里,艾氏在描述了法律和法学在西方文明中的崇高地位后,指出:“在亚洲的另一端,中国在她已经建立起来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强大有力的体系之中……就只能给予法律和法理学以一个卑下的地位。虽然并不是没有司法机构,但她只是愿意承认自然秩序,并且只是推崇道德的准则。……中国虽是一个学者辈出的国家,但她所产生的法律评论家和理论家却的确很少。”所以,从文明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建立法治的道路不能不是一个与传统逐渐背离的过程。当然,这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最困难的地方。没有传统的支撑,很容易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与观念之间的脱节,损害法律的实效,降低国民对法律以及法院的信赖感,甚至导致局部的反复或倒退。不过,长远地看,法治和民主仍然是一条走向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话题转到死刑问题,索尔曼表达了对于中国近期死刑制度进展的强烈关注。我们知道,法国迟至八十年代初才废除死刑,在西欧国家里是最晚的一个。废除死刑的过程也是历尽艰难。我向他简要介绍了最近死刑复核权收回到最高法院等进展情况,也谈到自己主张必须尽快彻底废除死刑的论证依据。索尔曼谈到,事实上,法国在废除死刑前的许多年里,每年只有寥寥数人被执行死刑,但是,法国民意对于彻底废除死刑却是长期不能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界以及更多领域的人们向公众展现和分析死刑的弊害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都想到著名文学家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长篇散文《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公认文学家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大有作为。索尔曼饶有兴味地谈起不同国家对待死刑态度的差异,他说,在西方国家,关于死刑存废的讨论总是有一种宗教的背景。他认为,现代的天主教国家更愿意废除死刑,反而是新教国家——例如美国——更多的人倾向于保留死刑。这一点倒是我以前所不曾深入思考的。可惜时间太短,来不及跟他展开讨论了。
谈话之后,顺便在书店淘书,买得方继孝的新著《旧墨记》,其中收入谭嗣同拜帖(名片)一件,弥足珍贵。睹物思人,想起这位33岁就被执行死刑的烈士,不免感叹。假如那时已经废除了死刑,谭嗣同何至于血洒菜市口!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
与索尔曼先生谈中国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