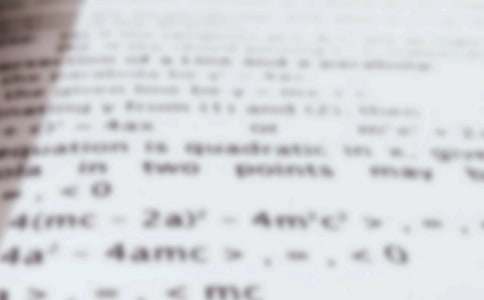老布鞋散文【最新3篇】
老布鞋散文 篇一
在家乡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位老者,他的名字叫做王大爷。王大爷是村里最受尊敬的长者,他总是穿着一双旧旧的布鞋,走在乡间小路上。这双老布鞋已经陪伴了他整整三十年,见证了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每当天气晴朗,王大爷就会背起一筐菜,穿上那双老布鞋,走进村里的小菜市场。他总是笑容满面,与每个人打招呼,仿佛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动摇他的心情。人们说,王大爷的老布鞋踩在土地上,就像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传递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外地游客,他看到王大爷穿着那双破旧的布鞋,忍不住问道:“大爷,您为什么不换双新的鞋子呢?”王大爷笑着回答:“这双鞋子已经陪伴了我三十年,它们见证了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换了新的鞋子,我可能会觉得不习惯。”
外地游客听后,感慨地点了点头,他明白了王大爷心中那份珍惜和回忆。从此以后,王大爷的老布鞋成为了村里的一道风景,人们看到它们,就想起了这位坚强而温暖的老者。

老布鞋散文 篇二
在城市的繁华街道上,有一位街头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小刘。小刘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每天早晨,他总是穿着一双破旧的布鞋,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弹着吉他,唱着动人的歌曲。
小刘的布鞋已经破烂不堪,但他并不在意,他觉得这双鞋子是他音乐之路上的忠实伙伴。每一次弹唱,每一次演出,都离不开这双老布鞋的陪伴。人们常常在他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他的歌声像是一缕清风,吹散了他们心中的烦忧和忧伤。
有一天,一位音乐制作人路过小刘的表演现场,被他深情的歌声所打动,当他看到小刘脚下的那双破旧布鞋时,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他走上前去,对小刘说:“你的音乐很棒,但这双鞋子已经不能再支撑你的梦想了,让我来帮你换一双新的吧。”
小刘听后,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音乐制作人的好意。他说:“这双鞋子虽然破旧,但它见证了我音乐之路上的艰辛和坚持,我不想轻易放弃它们。”音乐制作人听后,默然而去,他明白了小刘心中那份执着和坚守。
从此以后,小刘的老布鞋成为了他音乐之路上的象征,人们看到它们,就想起了这位执着而坚强的街头艺人。
老布鞋散文 篇三
老布鞋散文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咿呀学语到悄然老去,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事陪伴我们的一生,值得我们去记忆,让我们无法忘却。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一直是穿着妈妈纳的布鞋长大。都说母爱似海,而母爱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除了妈妈做的饭,无疑就是那妈妈一针一线纳出来的老布鞋了。
纳鞋底,做鞋这些活计,和蒸馍馍做饭一样,对于我们北方农村的女人来讲,这是一种极为普通却极为重要的手工技艺,也可以说是考量一个女孩子是不是手巧,会不会过日子的重要标准。如要是一个女孩子不会做饭,不会纳鞋底,就会被看作家教不好而遭人轻视。日后嫁到了婆家,在家里也会没有地位,因为这个女孩子一旦嫁过去,成了家庭主妇,那么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公公婆婆,老公孩子,甚至小叔子,小姑等的鞋都要靠媳妇的一双手做出来,如果这家的媳妇做得一手好鞋,老爷子,老太太穿着儿媳妇纳的鞋,出门在人前头也能昂起头。因此,在我们乡下,无论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大嫂,大娘们,无不有一手纳鞋底的好手艺。
我小时候不懂事,妈妈做好了鞋,我只知道穿,等穿破了,一双崭新的布鞋又蹬在了脚上。我的脚长得又瘦又长,又是男孩,爱疯,所以穿鞋也费,几个月一双,往往是其他部位好好的,脚趾头先把鞋前头磨破了,从前头拱出大拇哥来。我妈妈常爱念叨的一句话:
“你的脚是刀子?吃鞋呢!
”现在每每想起,心里便会有些许暖意。
记得有一次,我脚上的鞋又顶破了,却舍不得马上换新的,就穿着露脚趾头的破鞋去地里干活,一不小心脚趾踢在了刚收割完的玉米秆的茬上,顿时鲜血就流了出来,当时疼得我两眼发黑,尽管后来包扎了,还耽误了两天上学,却还是感染化脓了,脚趾肿得厉害,到后来连趾甲也掉了,长出的新趾甲变得很厚。那年我好像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也是我关于布鞋的一点点记忆!
我们乡下的布鞋,男的用黑灯芯绒做鞋面鞋帮,讲究白底黑帮,穿上很精神。女孩的鞋则一般用暗红色带小点点的灯芯绒做,鞋口那里会有个搭袢。棉鞋要复杂些,鞋帮比较高,再续一层棉花,在鞋帮两面钻几个气眼,系上鞋带,下雪的时候穿上很暖和。
一双新布鞋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穿的方面。男孩去女孩家里相亲,一般都会穿一双新鞋,女方家里会根据他脚上的鞋来判断未来的亲家是不是过日子的好人家。同样,没过门的女孩去男方家里一般也会留下两双自己做的布鞋送给老人,男方的家长也会根据这两双鞋来断定这女孩子过了门是不是过日子的好手。
如果男孩和女孩已经订了亲,男孩要去当兵或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女方送行的时候,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贴心话,但一双亲手做的布鞋是必不可少的。有心并且手巧的,还会在包裹里放两双自己做的鞋垫,那鞋垫用鲜红的布做成,再用缝纫机踏出一道一到密密的线,上面用彩色的线绣上鲜绿粉嫩的并蒂莲,鸳鸯什么的,以示同心。男孩子穿着这样的鞋,无论走得再远,一颗心总是和女孩子在一起的。
家里有老人去世了,脚上必定有一双厚厚实实,合脚熨帖的,白底黑帮的老布鞋陪伴着他走向去往天堂的路。。。。。。
做老布鞋必须要有好线,因此首要任务是纺线,把弹的蓬蓬松松,软软绵绵的棉絮撕成一尺左右长,在一根光滑的高粱秸秆裹好,一卷,轻轻一抽,一根纺线用的棉絮条就做好了,这样要抽好多根,我记得妈妈那时候要装一笸箩,等到晚上我们都睡了,妈妈会坐在一辆很旧的纺车前,一手转动着纺车的把柄,另一手在纺车另一端的一根铁锥上捻着棉絮,眼看着一根细细白白的棉线就那样轻巧地从妈妈手中的棉絮条牵了出来,然后牵棉线的手再轻轻往回一放,棉线便绕在了那个铁锥上,随着纺线车子的转动,眼看着白生生的棉线团慢慢地变得大了起来,一头粗一头细,像一个小巧的玉米穗子。
在我们乡下,纺线,做鞋是闲暇时做的活计,不能占用白天在地里忙的时间,只能在晚上或是下雨天和农闲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天热的时候,妈妈会把纺车搬到院子里,在月光下纺线,我睡在院子里的凉席上,看月亮在大朵大朵的,棉花一样的云彩里穿行,院子里的光影时明时暗,熏蚊子的艾草静静地燃烧着,白白的烟雾伴着淡淡的药香在无声地轻轻飘荡,偶尔会有萤火虫带着点点簇簇的亮光飞舞。凉爽的风吹过,巴掌一样的杨树叶子哗哗作响,纺线车“嗡儿——嗡儿——”地轻声唱着。现在想来,这单调却悠扬的纺线声就是伴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最为美妙的音乐。
线纺好了,几股棉线挂在一个一尺左右,光溜溜的木槌上,上面有一个带钩的细铁棍,快速转动木槌,上面手一搓,一根细细长长的,纳鞋用的棉绳便做好了,这一做就是十好几团。
有了细绳,接下来就可以做鞋了。在我记忆里,好像先是做鞋样——拿一张随便什么纸用笔在上面画出鞋底和鞋面的样式,尺寸,再把剪好的鞋面的纸样比着在黑灯芯绒布上剪下来做鞋面。
做鞋底的粗布要剪好多层,所以这样的老布鞋也叫做“千层底”。把一层层粗布均匀地涂抹好浆糊,抚摸平展,然后贴在门板上晒干,取下来,这个叫“袼褙",按照鞋的大小剪下来,用白布包边就能纳鞋底了。(大致就是这样的,记不很准确)家里手巧的女人不用尺子量,就能准确剪出鞋底的大小,做好了穿着保准合脚。
纳鞋底是我们农村最常见的一个场景了。在田间地头,在打麦场里,在家家户户的门口,尤其是到了冬天农闲时,吃完了晌午饭,暖暖的阳光懒洋洋地洒落在家户的院落里,村里的巷道里,汉子们在打牌,抽烟,谝闲传,(就是聊天)小孩子们在四处嬉笑打闹,群鸡们在粪堆上,脚底下啄食。谁家的猪从圈里跑出来了,到处乱跑乱拱,有人在呵斥。家里的女人搬小个板凳,或坐在门墩上,一边和对门的女人唠着家常,一边纳鞋底。
一双好鞋底差不多有半寸厚,很结实,先拿锥子把鞋底使劲扎透,再把拖着细绳的针从针眼里穿过去,然后轻巧地一拉再一拽,“嗤儿——”一声,白生生的鞋底上就留下一个小小的针脚,女人们就这样一针一针地在鞋底上纳出密密实实,排列均匀的针脚来。
纳鞋底时左手食指一般会戴一个“顶针”,和戒指差不多,比戒指宽很多,上面有一排排的'凹点,是为了防止针扎到手。有个歇后语叫做“纳鞋底不用锥子——针(真)好”,就是指这个说的。
鞋底纳好了,用白布把鞋底包一个面,就开始上黑灯芯绒的鞋面,——一针一针,扎扎实实地纳,密密地缝,我想,她们一定是把自己对家庭的爱,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一并纳进去了吧!
上好了鞋面,再在鞋口两边各镶上一块很有弹性的黑色松紧布,这样脚稍微肥了瘦了都能穿。
鞋做好了,但还不能穿,新鞋太紧,要用一块专门为了撑鞋用的,很光溜的木头楔子塞进鞋里,拿锤子往里敲,目的是是让鞋子松软些,宽松些。这样,一双白底黑帮的乡下老布鞋才算真正做好了。家庭富裕的人家会根据家人的情况做好多双,放起来,里面放些卫生球,以防虫子蛀。
这样做出的鞋,没有皮革的水光溜滑和斑斓的色彩,也没有那些摆在大商场的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大牌鞋来得气派华丽,它朴实得宛如一把泥土,穿着这样的鞋,心里是那样地踏实,平和。它透气,舒适,不会捂脚,更不会得脚气,走再远的路脚也不会累。我们乡下人就是穿着这样的鞋子,一辈又一辈走过了春夏秋冬,风风雨雨。。。。。
我有幸看过流行于陕西华阴一带的老腔戏,据说这戏从秦代就有了,完全是农民忙碌农活之余自娱自乐的一个剧种,演员都是乡下的农户,所用的乐器就是平常农户家里的用具,甚至连长板凳都有,用一块木头有节奏地击打,其唱腔高亢而苍凉,粗旷而豪放,听之观之,犹如行走在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一股凛冽的秦汉之风迎面而来,让人的心灵为之沉醉。这老腔就和老布鞋一样,摒弃了雕琢和浮躁,远离了商品化气息,宛若一段剖开的原木,都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东西,而最本质的,往往也是最为珍贵的。
时光在流逝,许多传统的东西在渐渐地离我们远去。在如今的农村,人们的日子好过了,而会做一双好布鞋的,却越来越少了。都是买着穿,尤其是年轻人,觉得老布鞋“太土”,不爱穿。再就是做起来太慢,太费工,远不如去商场买鞋穿方便。我觉得其实这“土”,正是老布鞋的本质——像泥土一样厚重,朴实,因为这里面承载了祖祖辈辈千百年来对脚下的这块土地深深的眷恋和热爱——这也是一种文化!只是这样厚重的乡土文化正渐渐地被流水线上生产的,光鲜而华美的现代化商品的浪潮淹没。其实,被淹没的,何止是一双老布鞋?那鲜艳的窗花,农家织的厚实的土布,极具乡土气息的老戏乃至土灶,大笼屉蒸的形态各异,鲜灵活现的花馍等民俗文化也早已凋敝得七零八落了!——我想我们丢弃掉的不仅仅是老布鞋,老粗布这些手艺,更是丢掉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积淀下的,无比浓厚的血脉的传承!
若干年以后,我们还能从哪里寻找到记忆中老布鞋的那份厚实与朴拙?我很茫然,因为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