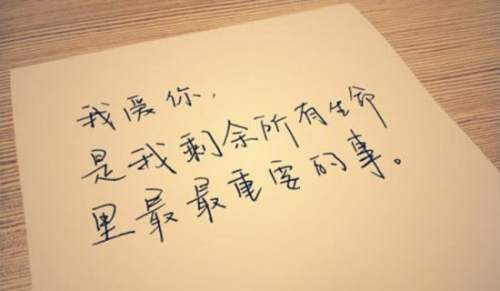贾平凹:说散文
如果综观中国的散文史,它的兴衰沉浮有一个规律,就是一旦失去时代社会的实感,缺乏真情,它就衰落了。一旦衰落,必然就有人要站出来,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改变时风,这便是散文大家的产生。
在中国,散文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文学形式,读者多,作者多,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谈谈自己的感想。我不知道前边的几位我所敬重的散文作家和散文研究家都谈了些什么,我惶恐
关于散文的那些道理,差不多的人都知道。轮到我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提出来呢?世上的事往往是看似简单的却是最复杂的,一个人的能力如何,就是看是否能将最复杂的事处理成了最简单的事。越是难以治愈的病,越是在这号病域里产生名医,比如有著名的治癌专家,治乙肝专家,但绝对没有一个是治感冒的杏林圣手。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我能谈出些什么可以让你们记录的东西,在这个晚上,我只以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说说我的一些体会来浪费你们的时间。
我讲九个问题。
一、关于改变思维,建立新的散文观。
其实,建立新的散文观,并不仅仅是散文,而是整个的文学观念。为什么我首先讲这个问题?如果初学写作者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了,但你真正地从事了写作,文学观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主办着一份散文杂志,叫《美文》,在一九九九年的一年里,专门在封二封三开辟了一年的专栏,刊登一些作家对散文的认识,也就是想了解大部分作家的散文观。从专栏的情况看,有一部分人写得相当好,也有更多的人仍糊里糊涂。我是指导着两个硕士研究生,在入校的头一个学期,我反复强调的也就是扭转旧的思维,先建立自己的文学观,起码要有建立自己文学观的意识,提供的书目中,除了国外的大量书籍外,向他们推荐读两个人的随笔,一个是马原,一个是谢有顺,这两个人的见解是新鲜的,但又不是很偏激。回顾现当代文学,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是怎样在政治的影响下成为宣传品,而新时期文学以来又如何一步步从宣传品中获得自己属性的过程。对现在的散文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五四时期散文,和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从新时期散文发展的状况看,先是政治概念性的写作,再是批判回忆性的写作,然后才慢慢地多元起来。但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说,散文在新时期文学中是相对保守的传统的领域,它发动的革命在整个文学界是最弱也是最晚的。中国的文学艺术,接受外来思潮而引发变革最早的应是美术界,然后是音乐,是诗歌是小说,然后才轮到散文。散文几乎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有了起色。随着整个文坛的水平的提升,散文界必然有一批人起来要革命,具体表现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争论。比如:散文是不是小说的附庸;散文是一切文学形式里最基本的东西,还是独立的;是专门的散文家能写好散文还是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专家将散文写得更好;它应该是纪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它是大而化之的还是需要清理门户,纯粹为所谓的艺术抒情型;是将它更加书斋化还是还原到生活中去,等等。正是这些争论,散文开始了自身的解放,许多杂志应运而生,几乎所有的报纸副刊都成了散文专版,进而也就有了咱们北大的这个论坛。
但是,我仍在固执地认为,散文虽目前很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革命的实质并不大,从主管文艺的领导,到出版界,作家、读者旧有的对散文的认识并未得到彻底改变,许多旧观念的东西在新形势下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如政治概念性的散文少了,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却多了,假大空的作品少了,写现实的却没有现实主义的精神,纯艺术抒情性的作品又泛滥成一堆小感觉,所谓的诗意改成了一种做作。我觉得,散文界必须要有现代意识,它应该向诗歌界、小说界学习。比如小说界对史诗的看法,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看法,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对诗意的看法,对意味形式的看法,等等等等。散文当然和小说是有区别的,但小说界的许多经验应当汲取。所以,我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一个最简便的办法是让别的文学艺术门类的人进入散文写作,我在《美文》的一个约稿的重要措施就是少约专门从事散文的人来写散文,而是尽一切力量邀别的行当里的人让他们为我们写稿。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与时俱进,如果套用这个词,散文质量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大,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的东西,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改革它的坐标应该是全球性的,而不仅是和明清散文比,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比,更不能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比。
散文界有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常常都知道某某是著名的散文家,但我们却不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作品。小说界,一部小说或许就使我们记住了这个作家,但一篇散文或一本散文集让我们记住的作家是非常非常的少。
我虽然在强调散文的现代意识,什么是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如果用一句话讲可以说是人类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怀的是大部分人类都在想什么,都在干什么。散文绝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它的任务也绝不是明确什么,它同别的文学艺术一样,是在展示多种可能,它不在乎你写到了多少,而在于你在读者心灵中唤醒了多少。作家的职业是与社会有摩擦的,因为它有前瞻性,它的任务不是去顶礼膜拜什么,不是歌颂什么,而是去追求去怀疑,它可能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世界对人生意义怀疑的立场上,而不是明确着什么为单纯的功
利去批判,所以,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种紧张愈强烈愈能出现好作品,不能以为这种紧张是持不同意见,而作家若这样以为又去这样做,那不是优秀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