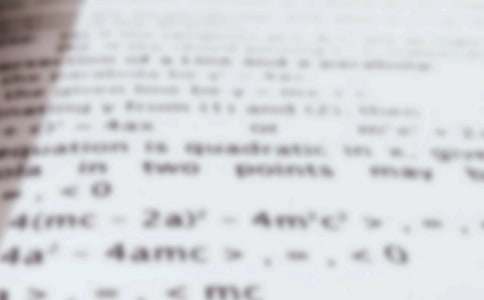散文禾花鲤(精彩3篇)
散文禾花鲤 篇一
在那个春天,禾花鲤成群结队地游动在清澈的溪水中,它们的身姿轻盈而灵动,仿佛是水中的精灵。禾花鲤长着一身金色的鳞片,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如同一颗颗宝石般闪耀着。每当太阳照射在它们身上,整个溪水都被渲染成了金黄色,仿佛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我常常躺在溪边的石头上,静静地观赏禾花鲤的游动。它们穿梭在水草丛中,灵活地摆动着鳍,仿佛在跳舞一般。有时候,它们会突然跃出水面,跃起的瞬间,水珠在阳光下闪烁,如同一颗颗晶莹的珍珠。我仿佛能听到它们欢快的歌声,轻快而悦耳。
禾花鲤是清澈溪水的守护者,它们守护着这片水域,让清澈的溪水流淌不息。在这个季节里,溪水清澈见底,仿佛可以看到禾花鲤游动的每一个细节。我想,也许这就是禾花鲤的魅力所在,它们如同一道靓丽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
禾花鲤是自由的,它们在水中畅游,尽情享受着水的清凉。我也想成为一只禾花鲤,畅游在清澈的溪水中,感受自由的快乐。或许,当我能够像禾花鲤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时,我就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快乐。

散文禾花鲤 篇二
禾花鲤,是溪水中的精灵,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礼物。在那个春天,我第一次看到禾花鲤,被它们那金色的身姿深深吸引。我仿佛被它们的美丽所迷惑,忘记了一切烦恼和纷扰。
禾花鲤是一种温和的鱼类,它们从不攻击其他鱼类,只是静静地游动在水中。每当我看到它们在水中穿梭,仿佛就能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安详。禾花鲤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感到温暖和舒适。
禾花鲤是溪水中的守护者,它们守护着这片水域,保护着水中的生态环境。它们就像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让这片水域充满生机和活力。每当我看到禾花鲤在水中游动,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欢乐和幸福。
禾花鲤的美丽让人陶醉,它们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生感激和敬畏。我想,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像禾花鲤一样,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珍惜身边的一切美好。当我们能够像禾花鲤一样纯洁无暇时,我们就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安宁。
散文禾花鲤 篇三
散文禾花鲤
雨后披蓑擒活鲤,风前弄斧伐枯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题记
农历六月,骄阳似火,天火水热,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也是一年一度最忙的双抢季节。呆在家里尚觉得热,更别说在毒辣的大太阳底下劳作了。但有什么办法呢?早稻成熟了,田垅一片金黄,得马上割转来。收割完后紧跟着要耕田插秧,赶在立秋前栽下晚稻。时间不等人,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只有个把月时间,收割,犁田,脱秧、莳田十分繁忙,功夫多得打结头,叫你歇你也不敢歇。
父亲说,作田的人,一年到头,也就这番功夫最苦了 。一个后生子,如果双抢都挺得住,熬得过,没有累趴下,就不怕了,就算学会了作田,再苦再累的农活都难不到他了。对于在田土里刨食的乡下老表,这番功夫做好了,做到了家,收成一般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再背也有八成,除非天老爷特别不帮忙,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双抢季节的辛苦,家在农村吃谷的人都深有体会。因为时间紧,活儿多,双抢季节,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男子人力气大,踩打谷机、挑谷担秧、犁田耙田打辘轴。妇子人耐力好,割禾捆禾草、脱秧莳田。老人在家晒谷收谷、烧茶炒菜,小孩子撸禾抛秧、送水送饭。各有各的分工,各做各的事。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分工,并没有固定,有时忙不过来,男子人也要做妇娘人的事,妇娘子也要干男子人的活,见子打子,见事做事。打从我记事起,直到我结婚后小孩出生,几乎每年双抢,我都在家里相帮,一次都没拉下。在读书时,双抢刚好是署假,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第一站在乡政府,会放农忙假。有时,我跟母亲喊苦,母亲就会说,怪只怪你不会出世,出在乡下,要出在石街上吃米,你就不要做了。
每天天一亮,正在我们睡得最香的时候,大人就会来把我和弟弟们叫醒。我们装睡不起,大人就会把我们的被单掀开,在屁股上或脚上打两下。尽管老大不情愿,我们也只能睁着半睡半醒的眼起来,带上东西,按大人的吩咐下田。如果饭捞起来了,我们还会抓一个饭团,边走边吃。因为人少不好做功夫,效率也低,特别是割禾,莳田更不要紧。一般双抢,都是跟我们几个叔叔家一起合伙,根据稻子成熟的早晚,讲好来,今天割你家的,明天割我家的。那些日子给人的感觉,就两字,忙,累。真的是忙,经常是田里的禾草都还没捆好担走,父亲就把牛赶来开始犁田了。禾坪上的谷子还没晒干,湿谷又担回来了,只好稍微晒一下,脱了水印,先收回来,堆在吃饭的厅里,过几天再翻晒。也确实累,做一天功夫下来,腰酸背痛,中午回来等饭吃,一身泥猴子一样,怕弄脏了席子不敢去床上,随便往地上一躺就能睡着。
但双抢时也有一件事,让我们充满了期望。那就是在割禾时捉禾花鲤,前提当然是要在稻田里放了鱼苗。在我们老家,有放禾花鲤的习惯。一般是春上插了秧,禾苗开始返青时,大人就会挑上鱼箩,去邻近的上犹县社溪圩买些鲤鱼苗。买来的鲤鱼苗根据田亩的大小三十、五十不等地放到田里,也不会随便放,要选择放水方便,排水也方便,四周的田塍筑得牢不会漏水的田。在每一个进水口和出水口都要用一蓬芦箕拦住,更小心的人家还会编个竹栅栏用木桩固定好,双保险,确保放到田里的鲤鱼既不会因为缺水死掉,也不会因为下雨天水漫田塍跟水走掉。
我们家有一丘田在蛤蟆石边上,喊十二担谷田,很适合放禾花鲤。离陂头近,水路短,四周的田塍都很牢固。地大水深,鲤鱼的食场好,每年放在那里的鲤鱼成活率高,很少少掉,且长得又大又肥。白色的禾花盛开时,我和弟弟经常会到那丘田,沿着四周的田塍巡逻,不时听得到鲤鱼跳起来吃禾花和禾苗上的小虫子的声音。运气好的时候还看得到游到田塍边的鲤鱼,看到我们来了,受了惊吓,迅速摆尾,忽啦一声,游进稻田深处。有时我们也会听错,把从田塍上跳到水里的田鸡的声音,也误以为是鲤鱼在觅食。这个时节,父亲会在田中间,把一株株水稻稍微移开,整理出一小段较深的水沟,让鲤鱼有更好的活动空间,并时不时从家里猪栏里捡来一畚箕猪屎倒在水沟里,既可以肥田又可以喂鱼。
只有一年例外,那年是个旱年,旷了好些日子没下雨,小溪里的水很小,跟小孩子的尿差不多,放一丘田的水要等好长时间,用老家的人话说,是没这么长的气来等。在我家十二担谷田坎下,是一个远房伯伯家的八担谷田,不知是因为被蛇还是什么东西钻了个洞,一丘田的水全漏光了。他不知因为忙什么,几天没去看田,等发现时田都开始干得开裂了,禾苗显得蔫不拉叽的。当时水稻正在灌浆,很需要水。他用锄头在我们家田塍挖了两三个大口,我们家田里的水和放在田里的鲤鱼,哗啦啦一下跑到他田里, 后来又从他田里溜到了小河里。因为陂头上没水来,我家田里的水一晚上被他放干了,即便有几条没走掉的鱼也被渴死了,或者被蛇吃了。那年父亲在田里放了近一百尾鲤鱼,最后一条也没剩下。
母亲说,伯伯完全可以不用这样做,通过我们家放了竹栅栏的放水口放水,新挖个口也可以,找几蓬芦箕和杂草拦住。这样我们家的鲤鱼不会走掉,伯伯家的禾也不会晒死。但伯伯太自私,只顾自己家的东西,不爱惜别人家的东西。为此,母亲说了伯伯几句。伯伯还振振有词,跟母亲吵了起来,是禾重要,还是鱼重要。无鱼就少吃点荤不会死人,晒死禾没谷割会饿死人,你负得了责。刚好父亲也在场,就劝母亲说,算了,事情都过去了,再吵也没有用,那些跑到河里的鱼也不会回来,就当没放,浪费几块钱。
还有一次,我们家和伯伯家的鸭子合在了一块。他家的鸭子少了一只,硬说我们家的一只鸭子是他家的,母亲经常招呼鸭子,对每一只鸭子都很熟悉,说她可以确定那只鸭子是我们家的,到青天下对天发誓都可以。但鸭子不会说话,母亲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只能干着急,生闷气,说,跟这样的人作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以后最好不要挨到他,拉屎都要跟他隔到几个坳来。事实证明母亲一点也没冤枉他,邻村的几个好吃懒做的白尾狗,无意中说起他们偷了伯伯家一只鸭子,藏到油槽下煮熟吃了。伯伯其实也知道这件事,表面上装着不清楚,白吃了我们家一只鸭子一点都不觉得理亏,好话也没听他说一句。
联系到这几件事,我和弟弟看到他都很讨厌,路上碰到了,不是万不得已,叫都懒得叫他了。以至于有一回,他家的牛没拴牢,挣脱了牛绳,跑到他们自己家的田里吃禾苗,刚好我跟母亲去做功夫路过看到。母亲叫我相帮去把牛赶出来,找棵树拴牢。我想起伯伯的种种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家的牛,不是我们放出来的,吃的又不是我们家的禾,关我们什么事。母亲仿佛对以前的事全忘了,说,住村坊,隔邻舍,能帮的还是要帮,再说,上到几代人前,我们还是一家。我说,当时,他糟塌我们家的东西时他怎么不会这样想。母亲知道我还在为那几件事生气,又说,人家是人家,人家的心在人家心里,我们管不了,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按我们自己的心做事就行。尽管心里有些不情愿,我还是去把伯伯家的牛从田里赶了出来,最后也没得到伯伯一句感谢的话。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更多的时候,田里的鱼在我们的小心呵护下,在我们的期望中,伴随着稻子一起成长。大人经常会支使我们到放了鱼的田里去看,有没有水了,进水和排水口牢不牢固,四周的田塍有没有缺口,会不会漏水。有时我们想偷懒,怕苦,不愿意去。父亲就会说,你们想不想吃禾花鲤了?不想吃就不要去。做什么事都要用心,用心了,庄稼才长得好,指望不要辛苦,不要付出,就有收获,我也想,可天底下也没这么好的事。
水稻成熟了,鱼也长大了,眼屎样的鱼苗放到田里,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到割早籽时,都能长成两三个手指大。只要是轮到割放禾花鲤的`田,不用大人叫,我们都会早早地来,从家里带个水桶,盛点水,跟在割禾的婶婶们后面捉鱼,有青鲤、红鲤和花鲤。因为田里的水满,还有些藏在稻草里的鱼,一时间没有发现,就只有踩打谷机时再捉了。因为抓鱼,耽搁了撸禾,赶不上趟,让打谷机空转,经常会遭到大人的呵斥。大人有时来了兴致,也会中途休息,参加一起来捉鱼。一边抓鱼,一边踢水,弄得一身都湿透了,一个个变成了泥猴子。在戏耍打闹中,缓解了身体的疲劳,稀释着浑身的热气,给辛苦、枯燥的双抢带来不少乐趣一些藏得更深的鲤鱼,要等到犁田或耙田时才能发现,但最终还是难逃被擒伏的命运。有几次父亲犁田回来,都用稻草串回一些漏网之鱼。
父亲会把一些体型健壮没弄伤的红鲤鱼,丢几条到我们家的小池塘里,到年底干塘时,就不是两三指大,可以长到一两斤重。大部分放在水缸里养起来,要吃随时捞几条上来。对那些养不活的,会剖好放大锅里烘干,烘成一块块的鱼巴子。如果没时间烘,还会摊在篾搭子上,放到外面日头下爆晒。因为有鱼,那段时间的生活比平时好了许多。奶奶会把鱼洗净,在砧板上剖好,除去肠杂,不再下水,带着血丝,和着葱姜在大锅里煎香,再跟青椒、丝瓜一起焖。奶奶比平时显得更加大方,一煮就是七八上十条,摆满一大铁锅。煮好的鱼都是用大砵头装,清香四溢,鲜嫩无比,舌头都会吞掉。用勺子盛一勺汤,不要任何菜,就可吃下一大碗饭。那味道而今想起来,依然让人回味无穷!在我看来,那些传说中的人间美味也不过如此。
如今,老家的人大都去了城里打工生活,只在逢时过节才会回来,村里仅留下一些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一畈畈的田荒了,没有人种,长满了杂草。难得的几丘田种了禾,也只是种一季中稻。双抢的概念没有了,一些后出世的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连带着放禾花鲤的习惯也没有了,鲤鱼早成了人不待见的东西,肉少刺多,据说如不除去背上的那根筋,还有毒素,大家都不爱吃。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想起那时的日子,双抢,还有禾花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