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娘散文
大阿娘散文
家乡习惯称姑妈为“阿娘”,大阿娘即是我的大姑妈,是父亲的堂姐。爷爷三兄弟,大阿娘是大伯公的女儿,我还有个从未谋面过的二阿娘,是我二伯公的女儿,父亲的亲姐姐,我的亲姑妈应是三阿娘。
据爷爷讲,大伯公大伯婆曾经生过三个儿子,都因各种原因夭折了,因此,大阿娘是大伯公唯一的孩子。大阿娘生于抗战前夕,如果在世今年刚好八十岁。大阿娘夫家在双庙村,离我家只有三四里地,那里有两棵千年老樟树,相依相偎,风雨同舟,看尽世间百态,阅过千年风云。
小时候,逢年过节,大伯公常带我去大阿娘家走亲戚。大阿娘家的老屋,在那条流向金清港入海而去的山水泾的北岸,依河而建,是典型江南畚斗楼,与两棵大樟树隔河相望。因此去大阿娘家,必先经过大樟树边的路廊,再过一座小石桥(后来该桥边上加造了一座水泥桥),右拐约一百米即到。大阿娘对我总是很客气,每次去,她都要拿出许多零食招待我,而吃饭总要摆上八碗。家乡习俗,农历七月半、冬至时节,都要祭奠天地祖宗,祭祀时要摆上荤素八碗,祭祀完再一家人享用。只可惜,在大阿娘家没有玩伴,因为大阿娘没有自己的孩子。
在家乡农村,嫁出去的女儿,只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才有走动来往,而跟堂兄弟、表兄弟姐妹一般不再来往的。我家却很特例,不仅大伯公常带我去大阿娘家,大阿娘与我家及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也是常有走动的,盖因大伯公没有儿子。在农村,没有儿子也被视作无后。大伯公因为喜欢我的缘故,很想爷爷将我父亲过继给他作儿子,而父亲是爷爷的长子,爷爷是有些不情愿的,如果我的两个叔叔之一过继给大伯公,爷爷也就一百个愿意了。
正是这个缘故,大伯公心底里是将我当作孙子看待的,每逢乡里集市日,总要给我带些糖果零食,平时也很乐意我去他家蹭饭吃,而我的两个弟弟,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因此,大阿娘在我眼里也是亲阿娘,大伯公在世时,大阿娘家的每次节日庆典,从没落下过我,甚至有一次,还带我去了温岭的蒋洋喝喜酒。
蒋洋是大伯婆的娘家,那次是大伯婆的侄儿结婚办喜酒。温岭是我们南边的一个县,明朝成化以前也属黄岩县,后析出自成太平县,因此,家乡人习惯称温岭人为“太平人”,太平人也讲黄岩话,只是语调略有不同。蒋洋离我老家有十几里地,近二十里,据说现在的温岭动车站,就在蒋洋这个地方,至于蒋洋属于泽国镇还是大溪镇,我就不大清楚了。
那天,大伯公大伯婆带着一应礼物,还有头年自家酿的两坛老酒,每坛五十斤,这是最贵重的礼物了,因此,父亲用手拉车,将我们送到黄岩与温岭交界的山坑岭下的湖头村地界,父亲就回去了。然后,大伯公在前面拉车,我跟在后面推,沿着泽大公路走了一段,后向南折入一乡村机耕路,又走了很久才到的,几乎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大概由于有喜酒吃的盼头,尽管走了那么多的路,竟不觉得累,到了蒋洋的舅公家,我自然受到了长辈们的一致夸赞。而大阿娘、姑丈,自己一路已先期到达。这次去喝喜酒,连喝了三天,在那边住了两个晚上。住宿是在另一个村庄,是大伯婆的妹妹家,我称之为姨婆。由于宾客很多,我们打的地铺,尽管如此,大家都欢天喜地,其乐融融。
这是我第一次去蒋洋,两年后,大伯公去世,让我去蒋洋舅公家报丧,我骑着自行车,凭着两年前的记忆,竟没有走错路,完成了大人交给我的任务。这是我最后一次去蒋洋,三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那里的亲戚都咋样了?
由于大伯公与爷爷哥俩的.感情太好,爷爷竟同意父亲过继,于是,请来大阿娘夫妇以及老舅公和族中老人作证,立了文书,我们家也做了搬家,搬到大伯公所属房子居住。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二叔主动要求过继,而这事竟得到大阿娘竭力支持,大伯公拗不过大阿娘的坚持,也只好同意,于是,又重新订立文书,重新调整我们的住房。这样过了几个月,大阿娘与二叔家可能产生了一些矛盾,彼此之间失去了信任,这是中国式姑嫂不和的典型例子,其实也很正常。此后,大阿娘要求我父亲与二叔,共同赡养大伯公大伯婆俩老,当然,过继一事就此作废,爷爷也绝不会同意两个儿子同时过继的。这样前后闹腾了将近两年,直到大伯公去世,都没有最后定局。期间,大阿娘是我们家的常客,老舅公常来我家调解此事,我也常见大伯公独自默默地叹息,而我的父母因不善言语,只能在无人时默默流泪。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老舅公跑断腿也未能如愿。
大伯公去世后不久,大阿娘一纸诉状,将我父亲和二叔告上了法庭,要求解除先前大伯公与我父亲两兄弟的赡养继承关系,大伯公的房屋财产,由大阿娘自己继承,大伯婆今后养老由她自己承担。当然,法院的判决不言自明,大阿娘作为大伯公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享有优先权,而大伯公与我父亲所订立的赡养协议,没有经过公证机关公证,没有法定效力。法院一纸判书,判决赡养协议无效,也判没了原被告之间的亲情。这样的结果,对我父母来说,也并不难以接受,难以接受的是亲戚之间的纠纷,以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我爷爷,从此,我们一家断绝了与大阿娘的亲戚关系。半年以后,大阿娘拆掉了大伯公的两间半老屋,将拆下的建筑材料,和大伯婆一起,带回了双庙村。这一拆,拆掉了大阿娘回娘家的路,这一拆,拆掉了大阿娘那东江河畔的根。
事后就事论事,大阿娘是欠考虑的,这事不仅违背了大伯公生前遗愿,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我爷爷的感情。爷爷对此事是绝不原谅的,因为,爷爷此前受到过一次亲情的伤害。爷爷第一次受伤害,来自我那个至今未曾谋面的二阿娘,她是我二伯公的女儿,二伯公被日本飞机炸弹炸死时,她只有两岁。此后二伯婆改嫁,每年都是爷爷种好粮食,送去给二阿娘,使其免受饥饿,得以长大成人。据我父亲讲,二阿娘出嫁时,父亲一家都去吃了喜酒的,此后也有来往,但二阿娘第一次婚姻没有维持多久,第二次嫁给路桥城里一个工人,从此就断绝了与我爷爷一家来往,爷爷在世时,每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一声感叹。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黄岩工作,想起大伯公曾经对我的宠爱,经请示父母,我去看望过几次大阿娘和大伯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大阿娘的老屋了,老屋已经拆了,我环顾四周,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有两间新建不久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新屋,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门口,那是我的大伯婆。我快步跑上前去,大声喊着:“阿婆,我是喜华”,然而,老人家看着我却没有任何反应。听到外面有说话声,大阿娘从立即屋里走出来,看到是我,十分的惊喜,拉着我进了屋,一边让座,一边问这这那的,我一时竟来不及回答。大阿娘告诉我,大伯婆已经老年痴呆,过去的事都忘了,过去认识的人,也都不记得了。我心中默想,大伯婆啊,你忘记了一切,等于忘记了烦恼,忘记得好啊!
时光又很快过去十多年,大阿娘夫妻俩已年过七旬,他们所在的双庙村全村被改造,成了“香樟湖畔人家”。老两口住上了一百二十几平米,装修一新的大洋楼,土地征用后,还积蓄了一些余钱,又有养老保险,日子过得很舒心,我的大伯婆也已作古多年。虽然姑丈一方外甥、侄子众多,不缺亲情,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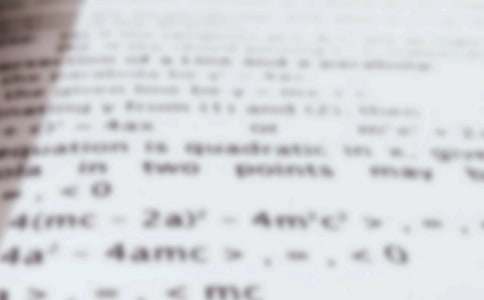
俗话说:相见一笑泯恩仇。何况亲人之间并无深仇,爷爷仍以他博大的胸怀,接受了这一中断二十几年的亲情回归。不久以后,爷爷九十岁生日,我们举办了一场家庭寿宴,邀请大阿娘夫妇也来参加,过去的所有恩恩怨怨,在这场欢乐的亲情盛会上,从此成为浮云。而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根植于我们心中,必将在后辈子孙中绵延流传下去。




